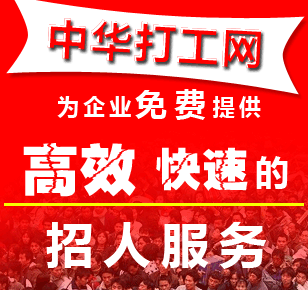南都与打工族“工伤探访”走进四家医院
发布时间:2012-06-21 11:30:40点击数:4936次
 ———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工专业老师郑广怀 《断指工老杨之死》之后,南都系列关注工伤维权报道持续发酵。 上周六,南都与佛山N G O组织打工族之家合作发起的“工伤探访”正式进行,16名志愿者前往佛山4家医院探访受工伤的工人,帮他们解决各种工伤疑问,赠送工伤权益手册等文字材料。志愿者中有9人是广州在校大学生,其余的来自佛山各个行业,有公务员、有保险公司的、有老师……(来源: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) 下午1点半,16名志愿者悉数到场。最早到的是华南农业大学三位学生,她们从广州赶来,怕时间赶不及,午饭都没顾得上吃。 “我不知道到医院探访他们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改变,但我想我们至少需要关注他们。”一位家住深圳的沈阳师范大学学生志愿者说。 一番自我介绍后,打工族之家负责人何晓波开始为大家讲解整个工伤探访的流程。他特意提醒,在工伤探访中,需要关注两个群体的态度:一是医生和护士,二是工伤者。对于前者,需要尽量避开,如果实在避不开,需要尽可能取得他们的同意,否则将会被医院驱赶出来。对于后者,则需要注意沟通的态度,尽量引起工伤者的共鸣,“遇到那些不配合的工友也很正常,不必强迫他们接受我们的工伤探访。可以留下我们的资料,下次再交流”。 工伤探访后,何晓波的团队还会对探访数据进行处理,分析出工伤种类、行业等特征,供政府决策参考。同时,还需对工伤者电话回访,了解其最新的需求,以便开展工伤探访服务。记者注意到在何晓波介绍情况时,志愿者纷纷记起笔记,有的还不断提出问题。 简单培训结束后,全部志愿者被分为6组,在打工族之家团队义工带领下,分别前往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、佛山市中医院、南海罗村医院以及南海创伤手足医院,开始他们的工伤探访之旅。 1 罗村医院 现学现卖,两女生拘谨上阵 周六下午2:45,打工族之家志愿者李煌带领两名中大社会学与社工专业学生史倩、陈雅晗,以及一名在佛山某事业单位工作的廖先生出发。李煌去年也曾被探访,那时他因工伤三根手指被压断,住院期间恰逢打工族之家到医院探访,接触后被感染,也做起了义工。 车上,陈雅晗认真地翻阅工伤知识的小册子,紧急补课。40分钟后,李煌一组抵达罗村医院。 探访的第一个工伤者由李煌带领示范。“你好,你是因工伤受伤的吗?”李煌推开病房门,问一位脚部受伤的年轻男子,随后进一步聊受伤的具体情况,陈雅晗和史倩两人站在一旁静静地听着,每人手里拿着一个本子,记下一些东西。 在这个病床探访结束后,陈雅晗和史倩决定亲自上场。在四楼另外一个病房门前,两人朝里面瞅了一眼,几名受伤的年轻人在病床上。史倩拉过陈雅晗说,轻声说,“我们进去吧”,陈雅晗看了史倩一眼,没说话。两人都迟疑了一下,随后,史倩怯生生地推开病房门,走到一位手部包裹着纱布的年轻男子身旁。 “你好,我们是打工族之家的,您是受工伤的吗?”2人问该男子,男子回答是后,反问她们俩“你们是哪里的”,2个女生说是打工族之家,男子似乎搞不清楚,2个女生紧张得脸都红了。旁边另外一名廖姓探访者帮忙解释说是志愿者,对方才明白。 两个女生学着李煌的样子,询问关于工伤的各种问题,看上去有些拘谨。在问每个问题时,她们称呼工伤者为“您”。由于男子右手断指,陈雅晗就蹲在病床边,帮该男子填写工伤探访表。在随后的1个多小时,陈雅晗、史倩两人已经和李煌分开探访工伤者,2个小时内,李煌这组共探访了10名工伤者,有3人填写了工伤探访表。 2 市中医院 “他们最需要的是情感慰藉” “您好,请问您是工伤吗?”微笑着走进病房,这是志愿者们的开场白。当日下午3时许,大雨降临前,空气压抑而憋闷。佛山市中医院新大楼11楼,手骨外科病房里,工伤者们大都半躺着,神情有些烦躁。墙壁上挂着的电视,音响泛散。 来自华南农大的志愿者何晶琳很快与一位工伤者交流了起来。“对工伤维权没有任何兴趣,现在的他最需要的,就是来自情感上的抚慰!”何晶琳对南都记者说,这也让她坚定了工伤探访的价值。她会尽量安排时间,争取在他手术前后再来探望一次。 打工族之家负责人何晓波说,他在多年的探访实践中也发现,这时候的工友对能获得多少赔偿并无任何概念,他们最多忧心的是未来的生活。因为工伤,他觉得自己倒霉,甚至产生自卑心理,将自己给封闭了起来。 “他们太需要有人愿意跟自己说说话!”何晶琳说,她发现对方手机屏幕上是一个漂亮的姑娘,但并不敢问那是不是其女友。在她看来,当一个人病着的时候,他内心的任何一处都必定是敏感而脆弱的。 3 南海创伤手足外科医院 保安驱赶“医院怕惹麻烦” “其实我很不能理解为什么保安要赶我们?”站在南海创伤手足外科医院的门口,李游显得有些无奈,“我们做保险时被赶能理解,但做义工宣传工伤维权也要被赶吗?” 李游是佛山中宏保险的工作人员,6月16日,他与同事梁于蓝、吕兆炳一同参加了工伤探访。刚刚进入医院的时候,三人显得很局促,看着社工给工伤者讲解维权知识,自己却不知所措。但20分钟后,他们也开始寻找工伤者攀谈起来,询问其家境、受伤情况、是否买社保等。吕兆炳说:“看着他们包扎的伤口,心里说不出的难受。” 李游则开始思考自己行业与工伤者的关系。他介绍,自己公司也有办理工厂团体意外保险的业务,但从没真正接触过工伤者。“我们都是直接与工厂打交道,没想到背后都是这么血淋淋的现实。”有些工友甚至连索赔意识也没有。“看来提倡探访真是有必要的。” 正当三人沉浸在尝试与思考中时,保安突然走进了病房,将他们请了出去。保安称:“这是我们的工作,我们也没办法。”三人则很不理解,自己做的是好事,为什么得不到体谅呢?与他们一同探访的社工则安慰说:“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了,医院就怕惹出麻烦,可以理解,但我们的探访仍要进行。”(来源: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) “打工族之家”五年之痒 缺钱少专业人员,更缺理解 背景:从2007年开始,打工族之家就到佛山市各大医院探访受工伤的工人。过去的5年里,打工族之家共探访超过4万人,登记在册的有4000多人,其中1000多人找到佛山打工族之家寻求工伤维权帮助,几乎全部维权成功。而探访的义工,也从最初何晓波一人孤军奋战,成长到拥有150多人的义工团队。 南都:为什么工伤探访? 何晓波:我受过工伤,三根手指断掉。住院期间,有志愿者到医院来探访。那时探访比较简单,就送一些工伤维权资料给我,没啥交流。对当时的我来说,这是我迫切需要的知识。而且我一个人在外打工,有人过来探访,心里挺温暖的。2006年7月,伤愈出院后,我就走上了工伤探访的道路,2007年成立打工族之家。 南都:5年来,遇到哪些困难? 何晓波:开展工伤探访五年来,遇到不少困难。第一,就是经费的问题。打工族之家虽然有国内基金支持,但是经费有限。很多参与我们工伤探访的志愿者,我们只能报销交通费。至于餐费等只能志愿者自己垫钱。第二,社工认可度不高,大部分医院还是比较排斥我们。他们为了保护病人,其实这方面可以理解,但是希望他们能够通融。另外,有一些医院是跟工厂有挂钩的,这样的医院工伤探访非常麻烦。 南都:能一直坚持下去吗? 何晓波:我会把工伤探访做下去。未来希望能够有更多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社工、心理辅导专家以及法律人士也加入进来。希望能以微薄之力推动工伤者境遇走向好转。 特写 志愿者:因为痛过,所以更懂 18岁的川妹子阿清,最近刚以@小清的玫瑰花园在新浪开通微博。她15岁从四川宣汉来到南海打工,去年8月被机器碾压两根手指,工伤维权之路并不顺畅。一周前,劳动仲裁刚开庭。因为维权,她认识了更多工友,并也开始探访其他工伤者。她的微博,记录下了这个过程的点滴。 “跟别人比起来,我真的没什么。每当看到那些断胳膊少腿的,我就觉得自己已够幸运了!”于是,从去年10月出院后,她就一直在做志愿者。 44岁的罗英资,孤身从阳江的乡下来到佛山工作。先是做家政,然后进了一家养老机构做保洁。对方承诺,一年后不仅包吃住,月薪还有2000元左右。但只做了20多天,她的手就开始出现肌肉萎缩等,去医院一看,说是用力过度。因为在养老机构里,每次都要搬重达百余斤的垃圾袋。工伤是认定下来了,但企业不服,将人社部门告上了法院。因为要7月份才开庭,于是他也做起了志愿者。 她说,现在最怕的就是将新伤拖成旧伤,那就难治了。如今她的双手已无法上举,还不能向后弯。“但能为工友们做点事,这就是我最高兴的。” 失去一只右手的谢敏祺,同样也是志愿者中的一员。参与探访的市民志愿者肖兵说,看到他用左手伏身认真填写工伤探访表,就很让他感动。 链接 排演维权剧,只为宣传更贴心 怎样能让探访有更好的效果,让更多的工伤者受益,是志愿者开展工伤探访活动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。李煌说,在做探访过程中,有些工伤者并没有多大兴趣,有些则对他们心存畏惧,担心受骗。 有丰富经验的高翔倾向于只单纯地传播信息,比如告知对方有这么一个机构和人群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,还比如可以做些必要的提醒,像注意保留好证据等,以及让他们尽量走法律程序。 这种机构介绍加维权技巧的探访模式,也是何晓波一直推崇的。至于形式,他希望还可借助戏剧等形式,来活跃工伤者们的生活。此前,他曾排演多场工伤维权剧,并饱受欢迎。“如果医院能提供这样的一个小场地,那将非常完美!” 一位20岁的工友因为一次机械事故没了一只手臂,他问了我的队友一个问题:我的手臂能治得好吗?当听到这句话时,我沉默了。看着他那迷茫和祈求的眼神,我知道他是多么渴望我们回答他能治好,可是我们知道他的右手手臂上截已经被压得粉碎,治好只是一个美丽的梦。没了一只手的他怎样面对今后几十年的生活?电视里的人在哈哈大笑,病床上的人茫然失措。他们亟须我们的鼓励,哪怕是一句安慰的话语,一个柔情的微笑,或是一个鼓励的眼神。 ———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大一学生许家霖 从探访情况来看,大多数工伤者对工伤认定以及伤残鉴定的程序完全不知道。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维权意识薄弱,我们的探访能提高他们的维权意识。我希望这个活动能继续下去,面对面交流,提供一些直接的建议和帮助,这比向他们做宣传然后让他们自己找门路要更有效。但愿微小的力量慢慢去推动大的改变。 ———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工专业大一学生陈雅晗 |